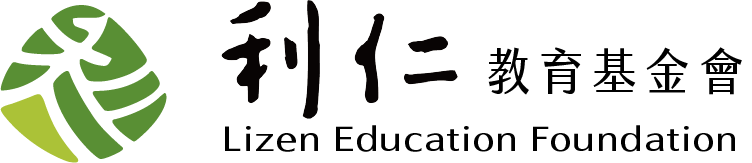
2022.02.14

大疫情隔離時代,人際疏離、家暴、種族對立和政治抗爭⋯⋯層出不窮,醫療照護、心理衛生與宗教界開始合作,強調「慈悲」行動與「自我慈悲」的價值與重要。
推動SEL的美國Emory大學,2019年進一步納入世俗倫理Secular Ethics的教育成為SEE Learning,在Emory大學SEE Learning網頁就開宗明義指出“This is SEL 2.0”,這是Emory University受到達賴喇嘛尊者啟發所開發的「社會、情緒及倫理教育」(Social, Emotional, and Ethical Learning)國際教育計畫。
2022.01.16台灣SEE Learning中心夥伴與利仁基金會董事、從台灣各處來到海拔900公尺的南投大鞍。台灣SEE Learning中心經歷一年半的籌備,由於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夥伴們都在線上見,2022年1月初與Emory大學簽約後正式成立,這是中心夥伴第一次實體見面。
一早陽光遍灑竹林,我們輕踩在落葉、碎石的小徑。雙手觸摸葉片、竹莖、石塊等,屬於森林的每一個物件,在定點駐足時刻,或背靠、或輕躺、有人凝視,有人閉眼,盡情大口吸氣、呼氣,安靜地聽著土地的聲音,也聽見自己脈搏的跳動。
許多夥伴自在地躺在竹林裡,看到竹梢在陽光的映照下發光,竹葉間的天空美的燦爛,大鞍的引導員說這是「森林之眼」,寂靜的天空對我眨眨眼,希望時間可以靜止,安心靠近自己的心。
上午全然打開感官系統,下午回到大腦。好好地認識神經系統,探索身體知覺,認識復原力區域。夥伴們倆倆實地做了「立即救助策略」,SEE Learning經典靜心活動—一分鐘接地(安住當下),一分鐘找資源⋯⋯等活動。
有帶領經驗的夥伴還帶著大家手繪一張「仁慈的時刻」圖畫,玩一個「心智罐」的活動。這看起來像美術課、實驗課的體驗,其實背後有啟動「領悟」與「反思」的內在歷程。有人說這彷彿是心靈遊戲的科學模式。
體驗之後,夥伴們分享熱烈心得,特別是一年半來SEE Learning的實作交流、不管是個人反思或教育現場的激盪、都溫馨而深刻。

──────────────────────────────
《心得分享》
●陶道毓校長
因為疫情的阻隔,我們這一群對SEE Learning志同道合的夥伴在2022年1月16日第一次相聚,有些夥伴還是初次見面,真是一大快事!也為未來的合作和推廣墊下深厚基礎,利仁基金會還協助連結了跨領域的心理專家一起努力、彼此支援和互補,非常感動也深深隨喜!一定要多學習!也非常感謝法師們不辭辛勞前來陪伴、聆聽和支持協助!祈願大家所有的努力都能承接師長的心願!
●李貞儀老師
我與學生—拿著傘對著我的學生
透過SEE Learning的學習,讓我有機會看到經過我教室門口罵我粗話的學生,其實有個人的脈絡情境;特別是發現他曾發生不愉快的人際衝突之後,更加應證這些負面情緒不是針對我而產生。
事發隔天,這位學生的班級在早自修時間跑操場,他卻走進我的教室,面露凶光的拿著傘指著我,從門口一路進來,我站起來說:「怎麼了?老師可以幫你甚麼嗎?」學生搖搖頭。我說:「你們班現在不是正在跑操場嗎?你不在,導師找不到你會擔心的。」學生板著臉回說不會….後來竟然放下雨傘問我:「英文那麼難,你怎麼會想要當英文老師?」謝天謝地,他開始跟我聊了,我好高興! 謝謝SEE Leaning, 讓我覺察到身體緊繃、心跳加速的同時,能擴大情境和反應之間的空間gap,做出適當的回應,化解了當下可能會起衝突的緊張狀況!非常感恩在利仁基金會的學習。
我與女兒—解開&鬆綁
老師這種職業就像有個金箍咒,不免將子女的表現作為自己教育能力的展現、也很在乎別人怎麼看待;而女兒在跟我反應學校老師的狀況時,我以為我已經夠同理她了,她覺得我還是在講道理。她跟我說:「你當媽媽、愛我就好了!」
學習SEE Learning, 讓我反思到我不會自我接受,更不會自我慈悲;忽略人們其實是在一個大系統中相互影響成長的,而其中每個人都有創傷。我試著接受我自己,也比較能理解女兒。她以前很ㄍㄧㄥ,不太讓我抱她;現在竟然願意讓我抱她了!那天竟然說要抱我,看能不能抱得動我,也真的把我抱起來!好感動…非常謝謝以慈悲為基礎的SEE Learning拉近我與女兒心的距離!
●王麗雅老師
甜瓠瓜的餘香
2022年1月16日與推廣SEE Learning的夥伴相聚,前一晚先到雲林古坑桂林村過夜,當天的晚餐是一整桌有機蔬食料理,雖然都是常見食材:龍鬚菜、山藥、瓠瓜絲、山東白菜、天貝、豆腐、什錦巴西蘑菇湯⋯⋯,但這一餐居然成為一口一口品嘗美味的味蕾之旅⋯⋯,充滿驚喜!我邊吃邊想:原來龍鬚菜淋了味增之後竟然不澀⋯⋯;哇!山藥咖哩很星洲咖哩的風味;天貝可比美素魷魚絲!而平常不碰的臭豆腐鍋居然夾了兩趟、因為是不臭的香臭豆腐!最最特別的是瓠瓜刨絲竟然.還有甜味⋯⋯怎麼會這麼甘甜?忍不住想起小時候母親包瓠瓜絲水餃的幸福滋味..所有味覺的幸福感、現在都只能透過記憶品嘗⋯⋯;當天夜裡山上好冷,躺在被窩裡腦海裡浮現的都是瓠瓜絲的甜味,也在甜味中進入夢鄉⋯⋯。能提前一天進住是幸運的,幸福感已經被記憶中的味蕾所喚醒!更大的驚喜是:回去和主廚大姐分享幸福的體驗、以及前一夜整晚的繫念:怎麼瓠瓜是甜的呢?大姐說:那不是瓠瓜是有機佛手瓜!
隔天一早我們一群人進入森林體驗大地與植物的療癒力,下午並實際體驗SEE Learning!體驗靜心,覺察感受視覺、聽覺、嗅覺、味覺的身體訊息!
●陳以儒心理師
在南投大鞍竹海被森林溫暖療癒了之後、參與SEE Learning 團隊帶領的活動,感知自己身-心之間的訊息,也對自己愈來愈好奇,有一種想多深入了解的感覺。
帶回SEE Learning活動:「心智罐」,常藉此和孩子一起回顧一天的生活點滴;在描述的過程裡,一邊投入代表的物體、一邊反思自己創造的生活,原本有點不愉快的經驗,似乎成為中性的事件,也發現有許多美好正圍繞在自己周圍,心因而更加柔軟!非常感謝能參與這次的活動,獲益良多。
●林怡岑董事
最後發言的是利仁董事林怡岑老師,怡岑與蘇治芬立委、李綠枝執行長有社區營造、教改深厚的革命情誼,即使各自在專業領域發光、仍然彼此撐持。怡岑提到此時此刻能凝聚這麼多夥伴參與台灣慈悲教育、一定有特殊的意義和價值。她深受紀錄片「大腦故事」和現場大家的回饋所感動,綜合過去二十多年社造經驗和大環境觀察,鼓勵大家以「利仁」為平台、用去「去中心化」的方式進行台灣SEE Learning的推廣。

《對談》
心得分享過後,利仁的董事長甘銘源、執行長李綠枝、董事林怡岑,陶道毓校長、Ariel老師,兩位法師( 本對談有兩位法師參與,因SEE Learning非以宗教面貌呈現,本處先不寫出法師法名。) 、蘇治芬委員等繼續對談。
「去中心化」的議題引發後續熱烈討論,甚麼是「去中心化」呢?
怡岑說我們常常會期待、依賴有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或領導人來解決我們所有問題;也常常怪罪都是別人的問題、彷彿和自己沒有關係。最直接的就是說總統該怎麼樣、政府該怎麼樣?老師該怎麼樣?爸爸媽媽該怎麼樣?老闆該怎樣?….這其實是一個共犯結構、或者說是形成的因緣。「解構」就是去掉想依賴一個強有力的政府或依靠一個領導人來解決所有問題的心態。
我們身處的時代是一個去「去中心化」的時代、不管是科技還是社區發展趨勢。過去只有學者專家掌握論述發言權、現在自媒體或社區媒體無所不在、只要願意任何人都可以發表意見,不管你認不認同、鼓不鼓勵或接不接受。「去中心化」就是相信自己、同時也相信別人;「解構」或「去中心化」從自己開始、這也是最困難的部分,這和佛法中「自我覺察」相仿,要看清楚自己的恐懼是甚麼?看清楚這種恐懼來自何方?為甚麼要依賴別人?明明可以「明心見性」為何還要受制於人?大時代的趨勢讓我們反思、順應「去中心化」的過程。
因此「去中心化」的SEE Learning論述不是誰說了算!
怡岑認為「去中心化」的慈悲教育是讓各領域、各階層、各種年齡和不同教育程度、不同論述的人都可以從SEE Learning受惠,也都能各自表達感受想法,這是大資料庫的概念。「利仁」的角色是去創造平台、鼓勵大家用各自的角度去論述、累積三、五年之後就會形成資料庫,未來所有研究就可以引用、並指出這些論述是來自利仁基金會哪一篇貼文!說不定五年十年後今天大家的分享會被研究者所引用呢!將視野拉開、讓利仁作為平台、並多多鼓勵參與。
長期深耕兒童青少年心理衛生的以儒心理師說道,對能守住崗位不被擊退的中小學老師們表達甚深敬意,因為在這個時代光是要守住教育崗位就不是容易的事!法師甲很受以儒心理師感動、提到過去日常老和尚以觀功念恩和儒家思想協助老師們,現在順應時代的需要SEE Learning提供老師們選擇。法師甲說透過SEE Learning的學習,老師們能表達自己的需要、情緒和感受,當孩子們看到老師不是權威、也會開始同理老師。
綠枝執行長持續反思甚麼是「去中心化」?乍聽到「去中心化」就像聽到「去權威」般會讓人感到擔心!綠枝問「去權威」要走去哪兒呢?科學也是打破一言堂、批判之後再重新建立的權威;綠枝舉華德福教育為例,開放教育以一種溫和而堅定的態度作孩子的典範、也是一種權威。綠枝再引黃俊傑教授關於歷史研究的論述:史書是被書寫頒布的,歷史研究者要先去脈絡化、再提出新的角度再脈絡化,加入與時俱進因地制宜的元素。醫學以積極去除病兆為主,心理醫師和綠色照護員則以更多元更柔軟的方式去應對、也是一種權威;SEE Learning並非沒有權威,只是切入的角度是甚麼?要呈現甚麼面貌?
蘇委員認為「去中心化」有很多面向、就「小我」來說是「去我化」、大一點則是「去權威」(威權和權威不同)。蘇委員對歷史真相頗有感觸,提及新近國家檔案局提供的內容真實度或許百分之八十需要去脈絡和再脈絡化。而這個過程需要辯論、就是科學。蘇委員提醒社會必須有論辯空間才是自由社會,否則就是威權;因此「陰性力量」* 必須起來、大家有辯論空間。權威未必不好,權威也是社會秩序之一、例如某些時空下菁英集體領導有它的優點、很難說對或不對。
(註:分析心理學家榮格(Carl Gustav Jung,1875—1961)認為,每個男性內在都藏著陰性的特質(阿尼瑪Anima),女性內在也具有陽剛特質(阿尼姆斯Animus)。陰性力量指的是溫柔、療癒,與人和大地萬物產生連結、滋養與包容;陽性力量指的是邏輯、理性、認知、思辨、行動力和意志力等。)

法師乙先回應「權威」和「威權」的差別;法師提及剛出家時日常老和尚說佛法就是「權威」,當時深受衝擊!老和尚說西方科學史已經多次翻轉,例如古典物理變成現代量子物理、因為智慧手機發明又翻一遍。但2500年來多少聰明的佛教祖師仍然沒辦法翻轉佛陀所說的獲得快樂離開痛苦的方法、所以佛法是權威。我內心想知道真相、這涉及蘇委員所說:真相是甚麼?專家怎麼說、我自己怎麼去解讀?脈絡是甚麼?
法師乙說佛法探討真相,區分成世俗諦跟勝義諦二層次,世俗諦是我們所見因緣合和所展現出來的所有現象;勝義諦是空性的部分,指萬事萬物背後沒有常一不變的獨立存在性的存在,例如仔細去尋找杯子並不實有。若要獲得快樂避免痛苦,就要透由五根、意根去判斷如何趨吉避凶,這觀待觀察力和判斷力,以及真相的探討和標準,因此能區辨世俗諦和勝義諦就非常重要!法師乙想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家為SEE Learning付出的和出家人所做的是一致的。法師乙以法師甲離開社運夥伴進入僧團為例,社運時期法師甲與夥伴生死與共、當時的目標也是希望讓世界更好;之後法師甲進入僧團、並非拋棄理想和伙伴,而是找到一條讓自己或世界更好的道路,但都還在持續探討中。尊者開示的方便我們就去試,試試看自己會不會更快樂?能不能讓環境更好?所以需不需要去「去中心化」、怎麼去做、怎麼去辨別甚麼是真實的東西、是我想努力的方向。
綠枝回應「大腦故事」紀錄片中,一個科學家說:我們科學家和學習佛法的人一樣,都透過不斷探索或實驗證明找到科學證據或真相,這在佛教就叫做「法」。其他的宗教多半是信仰,佛法則必須透過自己實證、如果得到跟佛陀一樣的結論,就變成你自己的信念和「法」了。
怡岑再度闡述自己關於「去中心化」的想法:第一、若比較佛法和科學,自己會選擇相信佛法。因為科學需要證據,透過看起來「非常理性的過程檢視」來獲得答案和結果。但科學就像紀錄片,通常紀錄片的導演都有立場,科學也一樣有他的侷限,科學家的立場會影響科學假設、取樣和科學論述、結果通常趨近於他自己的定見。
「大腦故事」紀錄片中尊者以更高的智慧讓科學成為載體,幫助人們從另外的面向(科學)去認識佛法。怡岑說紀錄片的剪接盡可能都以科學家的角度為主,尊者從頭到尾都沒說他自己⋯⋯,似乎把建立信念的主動權留給親身實證的每個人,怡岑因此而受到很大的觸動和啟蒙。怡岑說雖然用科學來證明慈悲或心靈層次對世俗諦有幫助,但尊者三十多年來跟當代科學家對話,就是為了因應當代人迷信科學的根性;因為科學也是幫助入類的八萬四千法門之一,都是要幫助人類朝更好的方向發展。
怡岑建議推展SEE Learning的過程雖不免提及尊者,但這不是尊者的本意!雖然階段性或特定族群面前可以這麼說,但接下來以「利仁」作為平台,要回歸尊者初衷讓更多人受惠!每個人第一手的經驗都非常寶貴,若可以讓幾千、甚至幾萬個人透過實踐SEE Learning、透過自我論辯之後找到自己的答案、自己生命的意義和價值,就像今天大家分享的體會和內容一樣、都和尊者陪伴科學家的價值一樣尊貴。所有人都一樣重要!尊者的影片和大家的錄影都一樣寶貴!

綠枝提到和怡岑的共同點是,思考著該如何讓更多人可以了解SEE Learning?目標並非希望SEE Learning立刻變成顯學、變成潮流,而是思考該用甚麼方法推廣出去?就像「大腦故事」這部紀錄片這麼好,看的人卻不多、非常可惜。聖嚴法師的生命故事紀錄片引起的討論相對較多,未來利仁的SEE Learning中心也許可以用「大腦故事」紀錄片作為素材、跟社會脈動接軌、變成學校學生可以討論的教案?從科學教育的角度切入,用論辯的方式激盪思考是否更有公民參與的時代意義?
法師甲代表台灣參加SEE Learning會議,正式簽約成員來自全世界,捷克有一百六十幾個學校積極推動、墨西哥某些地區已經成為公部門政策。法師甲說SEE Learning是跨文化、全球性的;SEE Learning在2019年才公布教材,目前正在主流化中。推廣不免會遇到阻力,尊者說SEE Learning是教育改革4.0;台灣目前還是民間力量,不用權威可以慢慢說服,科學也只是一種方法,讓人們試用之後產生信心。Emory大學提到推動方式因地制宜,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或者兩者並行。
法師甲強調SEE Learning是提供一種選擇和機會給校長和老師,就像是一個禮物或快樂的良方,背後是尊者和很多科學家的努力,全部都公開且非營利;這些科學家包括Peter M. Senge或Daniel Goleman幾位學術權威,SEE Learning不是強迫推動、而是提供選擇的機會。因此接觸點可以很多、接觸面可以很廣、多管齊下,例如透過研究、評估等科學方法也是。法師甲認為推動過程一定會出現很多問題,因此需要很多老師一起參與、老師本身的實踐經驗才動人,就像福智教師營的義工;由於義工本身也是教師,學員看到這些老師的實踐樹立了某些東西而被觸動。SEE Learning也是這樣的味道,打開接觸面、讓參與者嘗試、透過Q&A和一群熱情的老師回答各種問題,可以見面、線上或電話交流,用熱心來融化和連結。這個時代沒有權威,靠一群熱情的人,目的是回到老師本身,讓老師獲得新生、孩子也得救。

蘇委員和法師甲兩位台灣和香港社運的領銜人物,對「權威」和推動SEE Learning之間的關係有同樣的興趣和思考,蘇委員指出台灣體制內外遍佈權威,台灣教師體制相對保守、要打破教師的「中心化」並不容易;若以「利仁」作為平台、靠著一群老師小眾的實踐、要如何形成力量?透過縣市首長的參與才可能快速見到成效?法師甲則認為先要以研究成果作為基底,例如以實驗學校作試點、然後做研究評估、蒐集研究數據和成果,有成績之後再向教育相關首長爭取;法師甲引用尊者的話:SEE Learning是兩百年計畫。教育改革是很慢的,大學研究團隊可以從小的研究案開始;慧貞老師也建議從參加L1促進者培訓的十個大學老師開始嘗試起。
最後,陶校長分享第一線行政主管的經驗,在很忙碌的狀況下,即使有足夠的經費和國外新課程、若沒有經過本土經驗的消化、貿然引入也可能失敗,之前建構式數學就是例子,台灣已經有很多失敗的政策和經驗。建議要像貞儀老師這樣真正戮力實踐過的教育工作者來推動,才能產生效果。法師乙引用真如老師等待孩子改變的教導回應曹校長,可以用十年等待一個孩子。法師乙說我們可以透過每天的練習累積經驗,並了解失敗的原因;加上很幸運的,可以請教有經驗的全世界的菁英,甚至直接請教尊者,然後在台灣嘗試,我們不急。銘源說不用急,但要積極,大家都笑了。
綠枝執行長總結過去多年實驗教育的經驗,一開始也是民間累積很多年的努力。蘇委員擔任縣長的時候推動實驗教育,透過地方力量辦好學校,讓學校留住學生、並與當地社區結合,學校也是社區一部分,互利共好。
慈悲是一種方法、也是目標,Ariel老師分享美國Kentucky州Louisville市,在市長Greg Fischer的帶領下發展成一個慈悲城市。或許有一天,慈悲可以從一個班級到一個學校、從一個學校到一個社區,再從一個社區到一個城鎮、從城鎮到社稷並擴及全世界⋯⋯。
(文字整理/李綠枝及小編群)